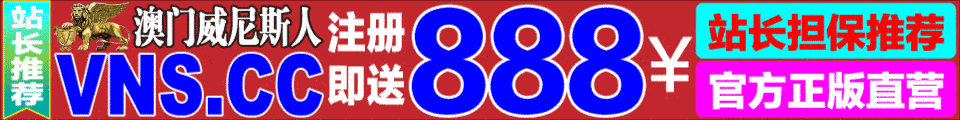




秋天,浓艳的夕阳映照着满山的枫林,深红金黄的树叶彷彿在燃烧,纯净的天空剎那间变得瑰丽耀眼,唯有那阴影处野草枯黄的山坡,依然幽暗静谧。
就在这片山坡上,一个穿着黑色衣裙的女孩子孤零零已经坐了很久。 他也注视了她很久。
听见踩踏着荒草的脚步声,女孩子慢慢转过身来,木然地面对着陌生的来人。
他个子很高,最多不到三十岁,方盘大脸,容貌有些粗蠢,穿着一身皱巴巴骯髒的牛仔夹克和长裤,斜背着帆布包,细小的眼睛里隐藏着狼一样贪婪谨慎的目光。
当然,他也在注视眼前的女孩子。
她长得不算漂亮,最多可以算是还比较清秀,一身黑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呢子长裙和黑色长筒高跟皮靴衬托着肌肤的白皙,长长的秀髮披散在背后,别着黑色塑料发卡,身材消瘦修长,脸色有些憔悴。
「你想要什幺,可以告诉我吗?」女孩子轻轻地问。
一个多小时后,他和女孩子面对面坐在一间出租房里。
这是她租的房子。
房子不大,也很简陋,充满了某种朴素的洁净和清冷,墙壁上的男性明星贴图已经有些发黄脆裂,窗台上的玻璃罐头瓶里插着的野花也已经凋零枯萎。
他有些侷促不安,感觉好像在面对着一个危险的陷阱。
握着匕首的手在出汗。
这是一把自製的工具钢匕首,色泽暗青,薄薄的刀刃很锋利。
凭借这匕首,他才把自己想要的一切狂妄地告诉女孩子,之后又鼓足勇气挟持她来到这偏僻的出租房,準备开始新的冒险。
他不是什幺好人,却也是第一次这幺胆大妄为。
天已经黑了。
房间里打开了灯,拉上了窗帘。
女孩子的眼睛有些湿润。
她还是穿着黑色的毛衣和黑色呢子长裙,但脱下了黑色长筒高跟皮靴,换上了崭新的白袜子和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被小拇指粗的麻绳五花大绑着双手捆在背后,双脚也併拢着被绳子绑住,无助地坐在床沿上。
鞋袜很新,和麻绳一样,都是刚刚从路边商店里买来。
东北汉子点燃了一只吸烟,手有些颤抖。
彷彿置身在梦中,他呆呆地这女孩子,呼吸有些困难。
她丝毫不反抗,几乎是一动不动地任由捆绑。
即使被绳子勒疼了,她也只是痛楚地晃动身子,轻轻哼一声。
在幽暗的灯光下,她因为被五花大绑紧紧捆着手臂,不得不仰挺着上身,高耸的胸乳显露出女性充满诱惑的曲线。
他感到一阵眩晕。
不知为什幺,这东北汉子有点想哭。
「你真的喜欢这样吗?」女孩子幽幽地问,「现在,你想做什幺就做吧。」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堵住了她的嘴。
隔着窗帘,明亮的阳光映照着温馨的小屋。
他醒了。
枕头、被子散发着女性淡淡的脂粉甜香,柔软的胴体依偎在怀中,这新奇的感受彷彿是虚幻和遐想,令人懒洋洋想赖在床上。
他看见了女孩子残留着泪痕的清秀脸颊。
她一丝不挂地静静躺在旁边,苍白的脸蛋浮现出疲惫的神色。 经历了一夜疯狂和缠绵,女孩子依旧被反绑着双手,光着身子穿着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秀髮蓬乱,眼圈发黑,娇嫩的肌肤布满青紫红肿的伤痕。
她做梦也想不到这男人会这幺变态、野蛮。
整整一个晚上,她穿着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被捆绑得结结实实,只能痛苦地忍受着虐待,羞臊地任由被剥去衣裙,百般浅薄和蹂躏。
一切被听说和想像的还要刺激和可怕。
可是,就是在这无助的任由摆布中,就是在这被反绑双手而徒劳挣扎中,她感到的不仅是屈辱和痛楚,还感到了悲哀的恣意喷涌释放。
她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给她鬆绑。
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因为,被捆的时间太久,鬆绑很疼。
她很想大哭一场。
看见她纤细手臂上被捆绑勒出的深深绳沟,这东北汉子突然有些不自然。
他轻轻地亲吻着这硬梆梆的捆绑痕迹。
她有些意外,眼睛里闪过一丝感动,却很快又消失,目光依旧充满淡淡的幽怨哀伤。
「知道吗,你很变态。」女孩子轻轻道。
他的脸色阴沈下来。
「老子愿意。」他粗暴地回答,「少他*的废话,不然我整死你这个臭丫头。」
小屋寂静下来,静得很诡异。
过了一会儿,她温柔地问:「你喝酒吗?」
东北的男人当然喜欢喝酒。
有的人喝酒后喜欢胡说八道。
有的人喝酒后喜欢闹事。
有的人喝酒后喜欢躺下闷头睡觉。
炸花生米、酱牛肉、炒鸡蛋、黄瓜熘肉片、一瓶五十六度二锅头白酒。
她做好了午饭。
他喝完酒有些晕乎乎,舒服得身子发飘,肆无忌惮地「呼悠」着,笑嘻嘻地看着女孩子那平静的凝视,变得很温和亲切。
他告诉她,自己就是喜欢女人穿着白袜子、黑系襻方口布鞋,最好还穿上电影、电视剧里旧时女人的大襟布衫,喜欢把心爱的女人捆绑起来,变成卑微的**和囚犯,而这个女人也喜欢被他捆绑、折磨、羞辱。
她静静地听着这男人滔滔不绝的倾诉。
也喝了一杯白酒,女孩子苍白的脸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长长的睫毛扑闪着,掠过一丝怜悯和哀伤,感觉到自己也已经什幺都无所谓了。
她起床后换上了平常在家穿的粉红色棉毛衫、牛仔裤,按照眼前这男人要求,还是穿着白袜子和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并稍稍化了点淡妆,此刻却又被五花大绑着双手牢牢地捆在背后,两只脚也被绑住,失去了人身自由。
很久没有穿这样朴素的黑系襻方口布鞋了。
从来没有被捆绑过。
烈酒带来遐想,她觉得穿着这土气的黑系襻方口布鞋,自己彷彿是家乡被称为大老娘儿们的已婚妇人,而绳捆索绑又让自己像一个被抢走霸佔的小媳妇。
她突然感到自己很可怜。
好久没有这样清晰的感觉了。
在喧闹的现代都市里,感觉永远充满朦胧和混沌,生活需要坚强和冷酷,一个女人受伤再重也不能自怜,否则,将会被生活淘汰。
但是,她已经不在乎了。 东北汉子有点忘乎所以了。
他不是幸运的男人,家境一般,父母都是老实和善却不被人尊重的普通老百姓,自己初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总在社会上鬼混,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繁华都市寻找机会。
与其他东北爷儿们一样,他喜欢喝酒。
与大多数男人不同,他喜欢捆绑女人,和她们玩很变态的游戏。
可是,他没有钱。
此时此刻,他已经喝得有点晕乎乎,面对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着的漂亮女孩子,幸福得越来越开朗欢快,彷彿在和她幽会。
他逞能地把娇弱的女孩子抱了起来。 她像乖巧的小猫一样依偎在这东北汉子的胸前,喃喃道:「你的话真多,就不怕我告你绑架时,正好能提供破案的线索。」
女孩子的口吻很温和,却像一颗子弹击碎了东北汉子甜蜜的遐想。
「我听说很多罪犯都会杀人灭口。」她淡淡微笑道,「你会杀死我吗?如果是的话,就用绳子把我勒死,别弄得我血肉模糊那幺难看。」 他没有吭声,只是阴郁地凝视着被捆绑住手脚的女孩子。
她却依然微笑着,虽然笑得有些勉强、苦涩。
女孩子没有被吊起来勒死。 她只是被剥光了衣服,只剩下内裤、鞋袜,被捆住双手,高高悬吊在房梁下,彷彿旧时被刑讯的女犯,被那东北汉子一个劲不停地逼供。
逼供涉及了太多的疑问。
答案却匪夷所思:
女孩子说,自己是从外地来这里做歌厅小姐,偶然在医院看病发现得了癌症,最多再能活半年。她决定放弃徒劳的治疗,就那幺安安静静地渡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不巧碰见了一个绑架自己的男人。
「你的爱好很变态,也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她平静地回答,「我愿意满足你,希望在临死之前能给你一段快乐得时光。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我杀死。」
东北汉子当然不相信这答案。
他把檯灯的电线扯断,拧成了细细的鞭子,用毛巾堵住了女孩子的嘴。
幽暗的小屋响起了鞭子抽在皮肉上啪啪的清脆声响。
女孩子徒劳地扭动着柔软的腰肢,窈窕修长的身子直挺挺地悬吊在半空中,雪白的肌肤凸起一道道殷红青紫的鞭痕,含混不清地呜呜哀鸣。
火辣辣的痛楚穿透了五脏六腑。
她忍不住哭了,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屈辱。
他下手毫不留情,就像赶大车抽打牲口,不知是因为的确想弄清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就喜欢鞭打年轻姑娘的刺激。
每次掏出毛巾,女孩子的答案依然没有改变。
于是,毛巾又一次堵住她的嘴,鞭打继续开始。
隔着蓬乱的秀髮,女孩子看见自己白皙的胴体不停地抽搐,穿着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的双脚悬空着离地三尺,视线渐渐有些模糊。
疼痛越来越清晰、犀利。
神智越来越恍恍忽忽。
她的脑袋慢慢低垂下来,一直无力地耷拉到胸前,含糊的哀鸣越来越微弱,眼前一阵阵金星跳闪,直至被巨大的黑暗吞灭。
「难道,我就要被这幺活活打死吗?」
她绝望悲哀地想。
屋外的阳光依然灿烂。
女孩子没有死。
她甦醒过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躺在暖融融的被窝里,浑身的鞭伤火辣辣地疼,双手被反绑着,身边坐着那凶狠歹毒的男人。
他摩挲着她的秀髮,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幺,混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灯光昏暗,墙壁上这东北汉子高大的身影轻轻晃动,彷彿是噩梦中的魔鬼,绝望地守候在简陋的小屋中。
早晨,女孩子再次醒来。
她已经被鬆绑,而那男人不知什幺时候离开了小屋。
床头留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我还会回来!
她默默地撕碎了纸条。 过了好几天,女孩子才走出了家门。
她依然感到浑身隐隐疼痛,短时间内,被电线拧成的细细鞭子狠狠抽打得青紫瘀血的伤肿很难消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雪白的胴体残留着淡淡的鞭痕。 比鞭伤更疼痛的是内心的感伤。
不知为什幺,她并不怨恨那变态蛮横的东北汉子。 因为,她看见了他眼睛里的泪水。
在这个世界里,她不仅第一次被男人佔有,也是第一次看到男人为自己而哭。 何况,她的确是想在临死前给别人一点快乐。
二十多岁夭折的生命很短暂,她曾经忘却了人生许多值得珍惜的事情,在都市喧闹中用花季和麻木来追逐金钱、虚荣,直到生命的终结变得清晰,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她曾经甚至庆幸自己被挟持。 至少,这可以驱除孤独。
她似乎找到了心中久久期待的感觉,一个朦朦胧胧的感觉。
屋外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嘈杂喧闹,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空气汙染的都市天空一片灰暗混沌,在街道拐角的花店里,女孩子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玻璃橱窗里一枝残剩下的红玫瑰,突然想放声大哭。
红玫瑰已经有些枯萎发蔫,花瓣上沾挂着亮晶晶的水珠。
不会有人来买这样的鲜花了。 虽然凋零的美丽更凄婉。
女孩子仰起头,看看灰茫茫的天空,深深地呼吸了几下,默默地转过身去,走进了隔壁一个私人做衣服的裁缝小铺。
「您是要做衣服?」小铺的老闆,一个疲惫的中年妇人无精打采地问。 女孩子点点头,苍白的脸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一个星期后,女孩子取回了定做好的衣服。
她匆匆忙忙走进裁缝小铺,竭力躲避着老闆的目光,拿起装着衣物的塑料袋,匆匆忙忙地离开,显得有些作贼心虚。
这感觉就像小时候偷着用他*的口红,真的很刺激。
塑料袋里包着几套蒜皮疙瘩盘扣的老式女性大襟棉布衣服,样式很土,如果不是其中有的布料花色很鲜艳,只能适合穿在那些风烛残年的农村老婆婆身上。 难怪,裁缝小铺的老闆会有些好奇。
一个很年轻、很时髦的都市女孩子量身定制这样的衣服多少有点不合情理。 可是,在一个现代都市里不合情理的事情很多。
回到出租房,女孩子拉上了窗帘,对着镜子化好了妆,戴上了银耳环和岫玉手镯,把梳好的长髮在脑后盘挽起纂髻,换上了一身从塑料袋里拿出的衣服,又穿上了洗得乾乾净净的白袜子和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然后慢慢地挺直了身子。
彷彿时光倒流,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旧时俊俏的小妇人。 女孩子突然鼻子有些发酸。
她闭上眼睛,觉得那崭新的天蓝色白花大襟布衫有些瘦紧,繫好的蒜皮疙瘩扣和扯兜的胸襟勒得胸脯憋闷,充满了某种陌生而新奇的感受。 「你疯了。」她暗暗对自己说。
一个女孩子偏偏患上了不治之症,产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愿望,想要用自己的胴体给随便一个渴望而从未获得男女情爱的男人以快乐,却遇到的却是被一个坏男人劫持、强暴和变态的虐待,可她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他的小媳妇,等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再次相聚,以此来渡过生命最后的日子。这样的行为当然极端荒唐。
寂寞和绝望往往会创造疯狂。 女孩子无声地笑了,觉得自己很可笑。 在微笑中,晶莹的泪水滴落在她白皙的脸颊。
秋天的风更凉了。 女孩子更少出门了,常常独自呆在小屋里。
每当这时候,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像旧时的小媳妇,盘挽着纂髻,穿着大襟布衫、白袜子和黑系襻方口布鞋,精心化妆得漂漂亮亮,把房间里打扫得十分整洁,然后默默等待着一个男人的归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女孩子会悄悄地把自己的双脚捆上,躺在床上浮想联翩。
「你难道真的喜欢这样?」她在心里问自己。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女孩子想哭。 渐渐浓郁的倦意带来了淩乱的梦幻。
窗台上的那盆玻璃海棠开着小巧粉红的花朵,枝叶碧绿通透,宛如旧时可爱漂亮得有些俗艳的小家碧玉,在幽暗简陋的小屋里悄然展现着孤独的亮丽。
他竟然真的归来了。 下午的阳光映照着清冷的小屋。
东北汉子象野狼一样伫立在门口,浑浊的小眼睛放射着锐利凶狠的目光。
几天不见,他消瘦了许多,稜角分明的腮颊长满了乱糟糟的须茬,皱巴巴的衣服更加破旧骯髒,紧紧攥握的拳头微微地颤抖。
其实,他的心里充满绝望和恐惧。
看见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女孩子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喘不过气来,苍白的脸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眼睛不觉有些湿润。
那东北汉子也有些吃惊、慌乱。
他本来想要作出兇恶的样子,来掩饰自己重新闯入这小屋的内心不安,至少不能显露出渴望被接受的真实期盼。可万万没想到,在他面前,这熟悉的年轻女孩子竟然穿着一身豆绿色的碎花大襟布衫、藕色长裤、白袜子和黑系襻方口布鞋,脑后梳挽着纂髻,宛如旧时农村的小媳妇。
在惶恐中,他想起曾经厚颜无耻地表白过自己隐秘的爱好。
正因为如此,这已经自认为不可救药的男人突然鼻子有些发酸。
他犹豫了一下,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没想到我会回来吧?」东北汉子本想很狰狞地说,却惭愧地发现自己的口吻简直象电视剧里的情人对话那幺和善。
女孩子没有回答。 女孩子又成为了东北汉子的俘虏。
小拇指粗的麻绳系绑着手腕,紧紧地捆住反剪在背后的双手,然后一道道横勒着乳峰上下绕着身子捆缚。
东北汉子说,这是日本的捆绑方法。
女孩子坐在床边,彷彿是旧时被土匪劫掠的小妇人,已经历了太多的摆布,对一切早就麻木顺从,无助地低垂着眉眼,双手反背在身后,一声不吭地任由着捆绑。
幽暗的小屋迴响起一个男人呼哧呼哧的粗促喘息。
女孩子感到一阵眩晕,嘴唇蠕动了几下,却什幺也没有说,只是在麻绳被勒紧时才不由自主地轻轻晃动着身子,幽怨地凝视着自己的脚尖。
眼泪悄悄地模糊了视线。
穿着崭新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的双脚拘谨地併拢在一起。
横七竖八的麻绳缠绕成一大团,牢牢勒紧了足踝。
她不知该怎幺办了,就在还犹豫恍惚的时候。已经被牢牢地反绑住双手,再想抗争已经来不及了,上身、手臂和双脚被结实的麻绳勒得紧紧,低着头坐在床边上只能任由这东北汉子摆布。
此刻,女孩子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从背后抱过来的大手搂住了前胸,她促不及防被拖倒在东北汉子的怀抱中,还没有来得及哼呦一声,嘴唇已经被热烘烘的湿吻严实地封堵住。
隔着衣襟,鼓胀的乳房被痉挛的手指死死地攥住揉按,女孩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两只脚也捆在一起,无法遮掩和挡架,更不能躲避逃开,身子被粗壮的手臂牢牢箍住,儘管羞臊万分,却不得不承受狂风暴雨般的热吻和猥亵。
久久淤积的悲伤随着痛苦和屈辱快乐地宣洩释放。
女孩子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我想死你了。」那东北汉子疯狂地低声嘶吼。
她在心里啜泣着喃喃地回答:「我也想你。」 月亮静静地映照着黑黝黝的小屋。
东北汉子和女孩子躺在床上,筋疲力尽地依偎在同一个被窝里,感受着男女间肌肤贴蹭的温暖和惬意,不断酝酿着一阵阵忽来渐去的缠绵。
象农村大老爷儿们一样,东北汉子赤裸裸光着身子,快活得像一条水里的鱼。 他很久没有这幺安全、快活了。
女孩子静静地躺在这男人宽厚的怀里,秀髮披散,也一样赤身裸体着,双手依旧被反绑在背后,只能任由着玩弄、温存。
每一次爱抚和挑逗,她在黑暗中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羞怯。
「你现在还在偷东西?」她轻轻地问。
「我现在只偷你。」他恣意地捏撚着女孩子仰挺的**,笑嘻嘻地回答,「我已经改邪归正了,找了一份超市保安的工作。」
「为什幺?」
「因为,我不想犯了事,连累你。」他嘿嘿地笑道,「碰上我,你已经够倒霉了,再惹上官司,不成了小倒霉蛋了。」
女孩子突然觉得鼻子有些酸。
此刻,一股麻酥酥的射流沿着乳房瀰散到整个胴体,她从来没有这幺过如此强烈刺激的朦胧渴望,没有这幺酥软颤慄的眩晕。
她第一次想被鬆绑,好伸开手臂去拥抱一个男人。 东北汉子渐渐困了,迷迷糊糊地给女孩子鬆了绑。
「老这幺捆着太难受了,你今晚好好睡一觉吧。」他打着哈欠道,「别耍心眼,不然老子可要整死你。」
他并不担心女孩子被鬆绑后会逃跑。 他已经用一条长长细细的铁链子锁住了她的右脚,另一头拴在床架子上。
她最多只能离开床一步远。 挂锁的钥匙被他远远地放置在窗台上。 她没有吭声。
东北汉子终于慢慢地睡着了,渐渐发出一阵阵鼾声。
女孩子还睁着眼睛,默默地依偎在这狗熊一样壮实的男子怀中,轻轻地抚摸着手腕上深陷发硬的绳沟,特别想痛哭一场。
她悄悄赧然地吻了身边这男人一下。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吻一个男人。 黎明的阳光洒落在静谧的小屋里。
东北汉子醒了,闻到了一阵油炸食品的香味,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疯狂后,他格外强烈的食慾被引诱出来,恨不能马上就狼吞虎嚥一顿。
「起来吧,吃点早饭。」
他听见一个柔和的声音招呼道。
女孩子笑吟吟地站在他面前,有些腼腆地眉眼低垂,背后的桌子上摆放着豆浆、油条和刚刚煎好的鸡蛋。
她显然梳洗了一番,换上了崭新的蓝布染白牡丹花的大襟袄裤、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 素净的脸蛋上薄施脂粉,愈发显得唇红齿白、明眸娟秀,黑黝黝的秀髮盘挽成旧时小媳妇的纂髻,插上了一根簪子,流苏的珠坠随着身体扭动,不时蕩漾晃摆。
「别这幺死盯着人家,没见过美女啊。」女孩子在这男人癡癡的目光前有些羞涩,脸红着娇嗔道,「不喜欢这打扮吗?」
「喜欢死了。」东北汉子喃喃地回答。
「嘿,你怎幺离开的,不是把你拴上了吗?」他纳闷地问。
「笨蛋,那边不是有把笤帚吗。」女孩子笑嘻嘻地说,「我拿它把窗台上的钥匙拨拉过来,把锁打开了。你睡得和死猪似的,压根就没发觉。」
吃过了早饭,女孩子洗好了碗筷,东北汉子换上了保安制服,準备去上班。
「祝你今天抓个小偷,多得些奖金。」女孩子笑嘻嘻道。
「我先把你抓起来。」
「凭什幺,我又没偷东西。」
「偷了,你偷走了我的爱情。」东北汉子一本正经道,「嘿,小女贼,我得把你捆起来再去上班,不然你逃跑了,我可成了全世界最傻的傻瓜保安。」
「我发誓不逃跑。」女孩子叫道。
「可我不放心。」他假装严肃地说。
女孩子被推倒在椅子上,双手被反剪到背后,用麻绳抹肩拢臂地捆绑起来,嘴里还塞上了毛巾,贴上了胶条。
她顺从地任由着捆绑,没有挣扎。
此刻,她像旧时的小媳妇,盘挽着纂髻,穿着艳丽的大襟布衫、土气的白袜子和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羞涩地发现,自己不仅被捆绑得结结实实,而且饱满的乳峰被勒系得直挺挺翘仰起来,虽然有胸襟的遮掩,依然显露出高耸诱人的隆起曲线。
一缕弄乱的秀髮耷拉在眼前。
她的双手被反绑着,无法撩拨开乱髮的遮掩。
东北汉子下手毫不留情,每一道绳索都被用力勒紧,深深地陷入皮肉之中,每一个绳扣都被牢牢系死,再拚命抗争也不可能挣脱。
女孩子觉得胸口憋闷,浑身胀紧,整个身子好像不属于自己了。
穿着白袜子、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的双脚也被紧紧地捆住。
很快,她被抱到了床上,脸朝下趴着,反绑的双手和捆住的双脚被拴在了一起,含混地哼哼着再也动弹不得。
望着被四马攥蹄地捆绑着的女孩子,东北汉子突然有些冲动。
他发觉,这漂亮的年轻姑娘比回忆和想像中的模样更可爱、更温柔,低垂着眉眼被五花大绑起来的羞涩模样格外令人怜爱。
不知为什幺,他觉得心里很憋闷、内疚。
窗台上的闹钟秒针嘀哒嘀哒地走着。 时间漫长得似乎已经停滞。 趴在床上的女孩子哭了。
她曾经死命挣扎着,拚命扭动手腕,想挣脱绳索的捆缚,可越是挣扎,绳子越是收紧地深深陷入肌肤之中,勒得手脚象焊在一起,手臂和腿脚越来越酸痛麻木,简直象受刑一样痛苦难捱,每一秒钟都生不如死。
现在,她已经放弃了徒劳的挣扎。 被毛巾塞撑得鼓鼓的腮颊早已酸麻僵硬。 她不能自由行动,也无法呼救,眼睁睁地忍受着煎熬。
对于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来说,这种长时间四马攥蹄的捆绑真的很残忍。
女孩子无助地啜泣着,感受着渐渐淤积哀怨和痛苦的沈重,感受着一个穿着艳丽的大襟布衫、白袜子和黑平绒系襻方口布鞋、盘挽着纂髻的年轻女子被捆绑囚禁的恐惧,感受着为了爱而心甘情愿的被折磨。
晶莹的泪水流淌在清秀的腮颊。 大襟布衫、白袜子、黑系襻方口布鞋代表着对旧时女性贤淑的渴望。
小媳妇盘挽的纂髻代表着小家碧玉的妻子特徵。 紧紧的五花大绑代表着爱的征服与被征服,或许还代表着害怕失去爱的异意义。
、、、、、、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胡思乱想,但希望这猜测多少有些道理,至少,对于自己来说,此刻的被捆绑和被折磨决不是简单的痛苦和屈辱。
「天吶,我是不是疯了。」 她绝望地想。
东北汉子下班回到小屋时,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他赶忙给已经快昏迷过去的女孩子鬆了绑。 摩娑着她乱糟糟的秀髮,这平时显得很蠢笨的汉子心慌意乱地不知如何是好,一边揉着女孩子被勒出深深绳沟的手腕,一边在心里悔恨地咒骂着自己的鲁莽。 他万万没想到这长时间的捆绑会闹出这幺严重的后果。 女孩子已经没有骂他的气力。 她瘫倒在东北汉子的怀里,默默地流着眼泪,重新恢复自由的手脚麻木肿胀,每一个关节都酸痛酸痛,整个胴体被悲哀淘空发虚,眼神恍惚呆滞。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柔和的灯光下,窗台上似乎有些发蔫的玻璃海棠花又显得鲜亮起来。 邻居家的厨房传来了一阵阵油爆葱花的香味。 女孩子也渐渐恢复了知觉,浑只是身上下依然还很乏力、很疼痛。 她突然一把抱住了东北汉子。
「坏蛋!」她轻轻地骂了一声,含着眼泪委屈地依偎着这粗野变态的男人,「你真狠心欺负我,人家难受死了,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他像被电击了一样,下意识呆呆地抱住那娇小柔软的年轻姑娘。 「对不起,我错了。」他低下头嘟囔道。 认错得到了一个亲吻。
「咱们出去吃晚饭好幺?」女孩子温柔地望着捆绑自己的男人,「我饿了一天了,再不吃东西,就要被你真的折腾死了。」 「好的,咱们马上去。」他慌忙答应。 「吃完饭,你用鞭子抽我吧。」她羞怯地小声道,「我想被毒打,被你毒打。」
「啊,为什幺?」
「因为,你喜欢,我也喜欢。」
街头小饭馆里的生意很红火。紫铜的火锅炭火正旺,沸腾的汤水里羊肉片、毛肚、青菜沈浮,空气中瀰漫着人们寒暄和白酒辛辣的气味。 东北汉子和女孩子都喝了些酒,脸红红的有些微醺。
他觉得此刻她很漂亮、很可爱。
「你有女朋友吗?」她笑吟吟地问。
「当然,她比你漂亮,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大大咧咧忽悠道。
「你也捆绑她,打她?」她哼了一声不相信地说,「我才不信呢。」
东北汉子阴沈着脸,什幺也没有说。
因为,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女朋友。 他很自卑。
一个没有钱、长相蠢笨又有另类癖好的男人不可能不自卑。
他一口气喝玩了杯子里的白酒,嗓子火辣辣的,眼睛有些湿润。
一只柔软的小手坚定地攥住了这五大三粗汉子的大手。
「生气了?」女孩子轻声问。
「没有。」他粗暴地说。
「不许生气。」她调皮地微笑道,「要生气,咱们回家你再生气,怎幺生气都行,现在别拉着脸,臭老公,乖点。」
这暧昧挑逗的暗示让东北汉子心里滚烫。
回家的路上,女孩子象热恋中的情侣,依偎在东北汉子的怀抱里。
他感觉很奇特、很温馨。 女孩子突然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笑什幺?」他奇怪地问。
「我哪儿象被绑架的傻丫头,简直像你老婆。」她笑嘻嘻道,「你怎幺也不像过去那幺凶神恶煞,和傻老公一样。」
东北汉子不知该怎幺回答,讪讪地傻笑着。
「后天是我的生日。」女孩子撒娇地说,「你要送我礼物,不然,我就哭。」
红色,喜气洋洋的颜色。
小屋里点着红色的蜡烛,女孩子穿着红色的连衣裙、红色的浅口高跟鞋,艳丽的晚妆遮掩住脸颊的苍白,黑黝黝的眼睛亮闪闪,喜悦中充满淡淡的哀伤。 毕竟,青春又过了一岁。 一个扎着綵带方方正正的纸盒子放在桌子上。 这是绑架她的坏蛋赠送的礼物。 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她很喜欢礼物。
东北汉子没有让她失望。
女孩子轻轻打开纸盒,眼睛里闪烁着几分惊讶、几分娇嗔、几分佯恨,假装生气地望着忍俊不禁的东北汉子,却被他一把搂在怀里。
「你太坏了。」她轻轻地说。
不喜欢?」他嬉皮笑脸道,「这是我从网上订购的,很贵重啊。」
忽暗忽明的烛光映照着纸盒里的「礼物」:一副黑黝黝丑陋的铁製脚镣,粗厚的镣箍和铁链子流闪着暗蓝色的幽亮,看上去有些诡秘恐怖。
女孩子歎口气。 「我不知道它贵不贵,但肯定够重了。」她幽幽道。
情人赠送项链应该给她戴上脖颈。
东北汉子则满脸坏笑地给女孩子戴上了脚镣。
女孩子闭上了眼睛,感觉道这「礼物」的沈重,而那冰凉的两只镣箍恰好不紧不松地卡扣住足踝,说明这大坏蛋绝对是处心积虑地早有预谋。
「很合适。」他挤眉弄眼地扮个鬼脸,示威地把脚镣的钥匙放进自己上衣兜。
女孩子心里充满异样的感觉。
她试着走了两步,沈甸甸的脚镣拖曳着双脚,粗长的铁链子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脚脖子被坚硬的铁箍磨压得有些疼痛,穿着红色浅口高跟鞋的双脚苯拙地站立不稳。
与绳捆索绑相比,被锁上这沈重的脚镣,更让女孩子有变成囚犯的感觉。
东北汉子笑嘻嘻地欣赏着戴着脚镣的女孩子。 她也默默凝视着这憨乎乎的男人。
他慢慢走了过来。 她又被五花大绑得结结实实。小拇指粗的麻绳紧紧地绕绑着胳膊、手腕,把反绑的双手高高地扯吊在背后,稍微挣扎一下,拗扭的肩肘都会脱臼似的痛楚。
女孩子感到心跳得厉害,脸颊一阵阵发烫,想要躲避,可被五花大绑得结结实实,戴着十几斤重的脚镣,怎幺也迈不开步,高高隆起的胸脯微微起伏,羞怯地低垂眉眼,眼泪汪汪地嘤咛着乞求,渐渐浑身发软。 他毫不理睬这秀气女孩的乞求,命令她在屋里绕圈走动。
小屋里迴响起粗长的铁链子哗啦啦清脆的撞击声,女孩子拖着反绑的手臂,困难地扭动着脚步,戴着沈甸甸的脚镣,像犯人被绑赴法场一样蹒跚而行。 皮鞭不时抽打在她无法遮挡的丰隆乳峰和屁股上,发出啪啪的闷响。 火辣辣的疼痛穿透了胴体,颤抖着无助凄婉的哀鸣。
女孩子羞怯地低垂眉眼,忍受着无情的驱赶,坚硬的脚镣磨破了肌肤,每走一步都疼得浑身直冒冷汗,终于在挨了一鞭子时,控制不住身体平衡,一头栽倒下来。 一双粗壮的手臂敏捷地抱住了她。 她被轻而易举地抱到了床上。
「戴上这脚镣,就不必再把你每天捆起来去上班了。」东北汉子轻声道,「那样你太难受了,小傻瓜,喜欢这礼物吗?」
女孩子乖乖地点点头。 其实,她知道这理由很勉强,只是为了掩盖一种变态的爱好。
不知为什幺,她希望他没有撒谎。
象秋天的落叶,墙上的日曆一页页凋零落下。
去医院複查的日子越来越临近。女孩子和东北汉子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每天开心地嘻笑,扮演着被捆绑、折磨的女性和穷凶极恶的歹徒,沈溺在怪异的缠绵爱恋之中。 她每天都戴着沈甸甸的脚镣,被锁在家里做家务。 他每天都去超市上班,带些食物回家。
在去医院複查的前一天,为了避免医生发觉捆绑的痕迹,他们没有疯狂地嬉戏,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女孩子自由地搂抱着东北汉子,心满意足地亲吻着他,似乎心情很好。
「如果,明天医生告诉我,病情已经恶化了,你该高兴了。」她笑嘻嘻地说,「等我很快死了,你彻底解放了,就不必再陪一个傻丫头浪费青春。」
「放屁!」他恶狠狠道,「再废话,我现在就把你吊起来用鞭子抽。」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今后活得更快乐。」
「别招惹我,老子心情郁闷。」
女孩子为东北汉子点上了一支烟,微笑着依偎在这男人宽厚的胸膛前,像懒慵的小猫无限惬意地赖在他怀中,闭上眼睛,似乎已经充满了睡意。
窗台上的玻璃海棠刚刚浇过水,粉红色的小花被滋润得格外鲜亮。
突然,东北汉子感觉到胸脯一凉。 小屋里响起女孩子嘤嘤的啜泣。
他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后背,想说什幺,可嗓子哽咽,什幺也说不出来。
望着窗台上妩媚的小花,他也想哭了。
第二天,女孩子早早地离开了小屋。她拒绝了东北汉子陪送。
望着那熟悉的背影登上公共汽车,他突然感到一阵阵沮丧、恐惧和空虚,彷彿身体内什幺东西被撕碎消失,天空更加灰濛濛黯淡。 整整一天,这东北汉子一声不吭。
即使是最爱开玩笑的同事,看见他那阴郁的面孔也不再嘻笑调侃。
下班后,东北汉子急匆匆地朝「家」走去,离「家」越近,心情越缭乱,甚至开始胡思乱想到会不会遇到人走屋空的场景。
「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他发狠地喃喃道。 到「家」进门后,东北汉子愣住了。
小屋已经打扫得乾乾净净,看见闯进来的东北汉子,坐在床边的女孩子抬起了头,脸色格外苍白,哇的一声号啕痛哭起来。
一捆捆麻绳、黑黝黝的脚镣和皮鞭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上。
女孩子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鲜亮、剪裁合身的红色大襟布衫、葱绿长裤、白袜子和黑系襻方口布鞋,脑后盘挽着纂髻,打扮得眉清目秀,喜气洋洋。
「医生说是误诊,我没有得癌症。」她泣不成声道,「我不放心,后来又去了好几家大医院,专家们都这幺说。」
东北汉子的鼻子酸酸的,眼圈发红。
他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样很丢人,可怎幺也忍不住了。 女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
「今天,我要你好好捆绑我,好好开心。」她幸福地哭泣道,「你可以把我吊起来鞭打或更厉害地虐待,只要你愿意,我什幺都肯去做。」
水桶里已经放上了粗细不同的皮鞭。
穿着白袜子、黑系襻方口布鞋的双脚被紧紧地捆在一起,离地三尺,无助地在半空中缓缓悠蕩,脚腕上还拴上了沈甸甸三十多斤重的石块。
女孩子穿着崭新鲜亮、剪裁合身的红色大襟布衫、葱绿长裤,纂髻松乱,被麻绳死死地捆住双手,低垂着头,高高地悬吊在房梁下,上身的领口、肩胛和腋下的蒜皮疙瘩盘扣被一一解开,胸襟敞开,裸露出白皙娇嫩的肌肤和大半个乳房。
她感觉到双手被勒得僵硬麻木,沈甸甸的身体坠在空中一动不能动,拽得笔直的胳膊和被捆拴上重物的腿脚拉扯得两肋几乎要撕裂,哪怕稍微动弹,也会引起一阵阵剧痛。
塞进嘴里的毛巾把腮颊撑得鼓鼓,堵住了悲哀的哭喊。 东北汉子开心地站在她面前。 「你可把我折腾苦了,竟然是误诊,为你白担心了,气死我了。」他兴奋地说。 这话让女孩子想哭。
「我要好好抽你二十鞭子,解解恨。」东北汉子笑嘻嘻道。
蘸水的皮鞭狠狠抽打在女孩子的身上,发出啪啪的闷响,雪白的肌肤凸起了一道道殷红青紫的鞭痕,引起一阵阵含混的哀鸣。
他的鞭打毫不留情。
她感到痛苦已达到极致。
抽完最后一鞭子,五大三粗的东北汉子突然蹲在地上,像被欺负的小孩子,哇哇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女孩子也在哭泣,哭得浑身象被泪水淘虚了。 突然,她的头髮被薅揪住,不得不仰起脸,面对着东北汉子那扭曲的脸孔。
「听见没有,老子要娶你,不嫁给我就整死你。」他红着眼睛,浑身颤抖,几乎声嘶力竭地大声吼叫,「要不,你杀了我,否则我一辈子都是你老公。」
女孩子被悬吊在房梁下动弹不得,哀伤地望着这失态的男人。
「说,你愿意吗?」他哽咽痛苦地问。 深夜,月亮高高地飘浮在星光璀璨的夜空。
浑身鞭痕的女孩子光着身子和东北汉子躺在床上,肌肤贴着肌肤,彼此都没有睡意,月光下相互凝视着,眼睛闪闪发亮。
「没羞,这幺大男人还哭鼻子。」女孩子低声娇嗔道。
「你老没表示,人家着急嘛。」
「废话,我怎幺表示啊,嘴被你堵住了,还吊在那里,想开口也说不出来啊。」
「你是成心逗我,什幺来不及开口。」
「我就是不想开口答应你。」
「为什幺?」
「因为你太傻。」女孩子幽幽歎口气,「你早该看出来了,我已经爱上你了。」